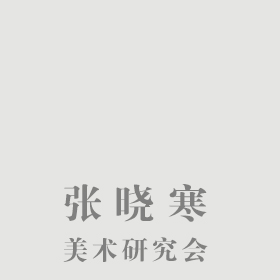虹 门 雁
文/张力
离离云,潇潇雨,弹指瞬间,深受尊敬和爱戴的我市山水画家、美术教育家张晓寒先生竟去世一年了。原有为他写传的愿望,却因他生前过于忙碌,去时又过于匆匆,终于未能再作长谈而嗫嗫于笔。但是毕竟与先生有十数载“忘年之交”,毕竟深受过先生的真诚教诲和身言影响,毕竟也听过些先生的嘘嗟慨叹——是啊,“一闭上眼睛,陈旧的岁月里总会唤起片片新绽的绿叶,在心里催化着缕缕梦幻的记忆。”先生毕竟向我们展示过这些记忆的剪影……
三十年代。苏北旷原上。
铅灰色的天幕掠过数行鸣雁,一座小小的古城镇孤独地立于秋野,灰黑色的古墙缝摆曳着几株干瘦的鼠尾草。城墙脚下蹲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抽着鼻涕,出神地盯着吊桥边那株老皂角树。黄叶在枝头上朗朗舞动。有几片落进了缓缓流动的护城河里,推着一圈圈好看的涟漪,向更远的地方漂去,就象那条小木船……
“咿呀咿呀”那条小木船从滔滔长江横过,从一道道河汊擦过,从一座座石拱桥下穿过,渐渐地荡进水色溟溟的太湖,荡进了名城无锡。小木船里就坐着小男孩和他母亲。
一条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街道。小男孩眨着一双好奇而惊喜的眼睛。无锡哟,对于一个从乡间小镇 来的孩子,你是个多么神奇泛彩的世界!
忽然,小男孩站住了。他看到了一家家裱画店,那里有水灵灵的墨荷、有奇峻的群山、有抚琴奕棋的道仙、有观鱼的狸猫……他看到了一家家泥人店,那里气势汹汹的泥虎、有高贵的泥公鸡、有渔翁牛童,最引人的却是那古朴笨拙大阿福、小阿福!他完全被迷住了,站住不走了。母亲用了好大力气才将他从店里扯出来。可是出了这家他又扑进那家,死赖着不肯出来。母亲只好动武了。
“哇——”地一声长嚎,小男孩泪水四溅,被扯着一步三回头地渐渐远去……
黄叶随流渐渐漂去,小男孩丢下了那段回忆。他站起来跑到内墙下,用小指头一个小团一小团地抠着粘土,然后捧着跑回河边。他也捏起小泥人了。
“宝才!宝才!”母亲在城里喊他的乳名。小城是那么小,在城当中用力喊,城外边能听见的。
“宝才!宝才!”可是他不愿意回答,他不喜欢回这个家去。
他从前的家在乡下一个小村子里,那里的河水好象更清,天色好象更蓝,还有一大片翠绿翠绿的桑树林。那里的家很安静,他有过一个连秀才都没考上的父亲,整天只是在书堆里打咳嗽。
那个父亲死了。
现在的父亲是个退役的北洋兵,和母亲在小城里开着一间小饭馆兼客店。现在的家是个吵闹的家,每天呼拳的酒客和住店的路人在那里嘶嚎笑闹。他总是远避这个家,他生性孤癖,人都说:“象他亲爹,那副读书人脾气。”
渐渐地,河边上摆出一支泥人的小队伍,有牛羊,有猫狗,当然还有大阿福和小阿福了。小男孩高兴地舒了口气,眯着眼看天,看看太阳能不能钻出灰色的云隙,透出点热来晒干这些小玩意儿。
他一边盼着太阳,一边拿了根小树枝在地上画了起来。这是树,这是房子,那是小桥……
忽然,一只光脚板踩在泥狗上,把它蹂扁了。又来了几只光脚板,大肆践踏这些泥玩意儿,连画在地上的树啊房子的都给抹掉了。
小男孩惊愕地站起来。他看见的是几个大孩子,一边顽劣地“哼哼”笑着,一边快活而轻易地销毁他所有的艺术品。
他没有反抗。他又重新到城墙下抠来泥巴,静静地专致地捏了起来……知道么,这就是他跨向艺术殿堂的第一步。
四十年代初。关中平原。
天色微明,朦胧的景色中,高高的大雁塔在长风推动的滚云中似乎也动了起来。在这座古老塔顶上立着一个青年和尚。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灰色的僧衣在凛冷的晨风中翻扑。
塔北面是绿油原。“绿油原,绿油原,黄土一片赤风旋”。在渐推渐远的旷原上,稀疏地散落着些高大光秃的杨树;寂寞地立着的一座座土丘,象一个个含混肿起的眼泡,在观察着这荒凉的世界,那是皇陵。那千年不散的阴魂在树梢上随风长号……
“年年清明陌上哭,春风吹湿破袈裟。”青年和尚轻轻吟诵了一句,轮廓分明的脸上,两行清泪顺着面颊缓缓流淌。他从古塔顶的砖缝中抓起一把黄草,在手中默默地撕碎,然后松开手指,看着它们纷纷飘飘飞散而去。
……
纷纷飘飘的鹅毛大雪在秦岭的千岩万壑中飞旋扑打。迎着雪花,一道热腾腾的灰流缓缓地雪路上爬动。“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一支悲壮的歌从灰流中冲出,这是一支流亡学生队伍。
一个围着破围巾,穿着破大褂的少年缩着脖子在这支队伍中走着。他扑眨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周围的奇景,一只冻得发红的手指头在衣襟上轻轻画着、划着。
“小心!”身后一个大个子同学拽住了他的后领,他这才省悟过来:脚下是一段硬朗而扭曲的独木桥。
他晃悠悠地跨过了独木桥,快步跟上了前边的同学,两年多来,他不知见过多少江河湖海,跨越了多少崇山峻岭!
从抗日的烽烟燃起之后,仅仅15岁的他就离开苏北家乡,颠沛在逃亡的难民队伍当中。国民党统治下的满目疮痍、饿殍冻尸的惨景在他心中划下了一道道深痕。同时,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深深地激动着他:那绿得发蓝的巍巍大山、弹拨心灵的涛涛大江、采石矶上的李白冢、鹤去楼空的黄鹤楼……
他拖着疲乏的步履穿越数省来到湖北。这里本来是他的目的地,他的大姐随军驻在这里。姐夫是个国民党军官。按照母亲的指望,他可以在这里落脚,靠着姐夫吃上一口饭。可是姐夫鄙薄的白眼,姐姐的陪小心,使他默默地卷起铺盖,穿过漫漫长街飘然而去。
他终于走进了西安“战时流亡学生接待处”加入了这支踏着滚滚黄土百里风雪的流亡队伍,过了秦岭到达安康。由于饥荒所迫,这支队伍又迁往嘉陵江上游的阆中,接着又缓缓流过雄伟奇峻的川峡大山、流过六百里曲迥险隘的古道、流过飘着冰棱的河、凌架天险的独木小桥、羊肠小道、还有那令李白惊呼“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后来,他又在严冬里卖掉了棉被,伸手接过同学老师凑来的一张张纸币,带着借来的高中文凭,从嘉陵江雨雪七百里到达重庆,投考“国立艺专”(抗战时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的合体),一路上,又是压雪的古松、穿空的兀石、巨崖峭壁险滩、拍岸的惊涛、峡谷中那震耳欲聋的隆隆回声、苍烈高亢的川江号子……他的灵魂在升华,在绞动着一股欲哭不能的激情。
这一切,无疑为他以后的艺术之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即使是十年、二十年、四十年之后,只要饱蘸情墨的画笔一提,这一切立刻就“冰河铁马入梦来。”
“国立艺专”里三年多的深造,在一大批名扬海内外的艺术大师的指点下,他才华毕露,画技日精。离开学校后应该说是路途顺畅的,由于大画家赵望云的推荐,他在户县师范教过课(今天户县农民画的兴盛发达不能说没有他的劳动汗水吧!)他还在西安“中华艺专”挂过教授的头衔;虽然才二十出头,却卖字卖画,严然有些名气了。可有了名气又能怎样?
“当时的天下一片黑暗、窒息、混乱。他感到痛苦,他想抗争,但又无能为力。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又是那样含杂,佛、道、石涛、八大的体系都兼而有之。是的,他所能采取的只能是一种消极无能的反抗。”
“大学生当和尚 !一个大学生在慈恩寺当和尚 !”西安城里闹哄哄地传递着这个新闻。
“年年清明陌上哭,春风吹湿破袈裟——”青年和尚忽然大声将这句诗喊了出来,惊起了一群噪噪的鸟雀。
五十年代。厦门鼓浪屿。
深蓝色天幕托出了这座名扬世界的小岛的黑色剪影。这剪影中依稀可辨的一处突起小山,那就是著名的日光岩。一边,还有座庞大的圆顶建筑,那就是八卦楼了。世纪初这幢仿似美国白宫玫瑰园建筑的主人,曾经膨胀起一颗多么宏伟浪漫的心!经过十多年努力,结果耗资巨大,还未完工就倾家荡产声败名裂而远走他乡。留下了这空楼架子。数十年的战争离乱,它历尽苍桑,风吹圆顶发出的古怪回声和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使它成为著名的“鬼屋”。“鹭潮美术学校”就暂设在这幢“鬼屋”里。
黑暗中“鬼屋”那抬眼可以直见四楼圆拱顶的地下室里正响着鼾声和梦呓的咂嘴声。那里蜷缩着上百名青少年学生。
一阵风吹来,伴着一阵吱吱嘎嘎的怪响,一块薄木板在圆拱顶下翻飘了一阵,砸在酣睡的孩子们身上,引起一片惊恐的尖叫和骚动。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重新躺下。
“看,张老师还没睡。”不知谁嘟了句。
从三楼最边的一个房间里透着一缕微光。
“是啊,他总是熬得那么迟。”
“张老师真了不起,是从京来的!”
“哎,要能看一眼北京就好 。”
孩子们似乎在那缕微光下安了心,他们议论着、议论着,不觉又睡下了。
在那透出来的房间里,一个中年教师正将一幅湿漉漉的山水画用个木夹子夹在板墙边的一条细绳上。他眯起眼凝视了许久,才呵了口气,从写字台下拿起一块用湿毛巾包着粘土,捻下一大块在手心搓了起来。在写字台一角,还放着一大迭学生的写生习作。
他聚精会神地捏起泥人来,第一个就是“大阿福”……童年的情景越长越近:家乡那棵哗哗摇的皂角树,那列古朴的城墙,小小的护城河,“咿呀咿呀”的小船,无锡城那条五光十色的长街 ……
他捏这泥人并不是为了重新品尝童趣,唤起遥远的记忆,而只是在一种紧迫感的催动之下:学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到处找不到接收单位。很显然,当时对绘画美术人材的需求量微乎其微,这样就使这所学校连生存都面临困境了。他和所有人一样焦急,说不出什么原因,他对这所学校有着一股很特别的感情。

春雨楼头尺八箫 张晓寒 1973年
他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于1953年来到这里。当时他还在北京的全国政协俱乐部工作,接到了西安的石鲁、敦煌的段文杰等等许多画友的聘请信。同时,他也受到了杨夏林先生的面见邀请。杨夏林是他“国立艺专”的同学,在画坛已有些名气了,在厦门鼓浪屿创办了一所“鹭潮美术学校”——现福建工艺美术学校。
但福建这个“蛮越之地”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却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吸引力。大概和他在国庆大典晚会看到的各地节目有关吧?那时福建带来的是歌舞“采茶扑蝶”和泉州的布袋木偶戏。这些节目给他带来了神奇的难以抑制的向往,他真的从北到南涉尽山山水水来到福建,来到鼓浪屿岛上这座荒凉的“八卦楼”。
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学生呢,大多来自附近不发达县市,很多还是农家子弟,被称做“内地仔”;教学经费如此拮据,上完课,他时常还得陪热心的杨夏林校长过海来厦门,四处找华侨募捐以维持这所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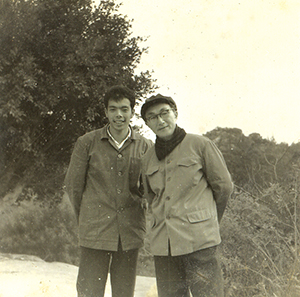
晓寒先生与张力合影
……灯下,把看着手上的泥虎,看着“大阿福”,都还不错,线条简练流畅,圆笨笨的,很可爱。对于一个艺术素养较高的人来说,要轻快掌握一种陌生的艺术门类并不太难。这就是行家们所说的“自觉”。行了,看来可以开捏泥人这门课了。其它工艺课再开几门,学校就从纯绘画美术的性质变为主要培养工艺美术人材。这样,学生就不怕没出路,学校也不会倒闭,然后再回过头来以艺养画,就什么都活了。
近来他已跑遍闽南地区,找来石码的刻木偶师傅许清风,找来漳州一位姓蔡的泥人师傅, 找来了年轻的泉州刻纸师傅徐耀坤等人。他还找来了穷困潦倒疾病缠身的彩扎老艺人柯石头,目前正张罗着给老人治病、接济生活……这些人,都将是学校的一批辅导师资了……
“张老师,天都亮了,你还点着灯!”不知什么时候门被推开了,几个学生和一大片晨光一起扑进来。他们一个个光着脚板,这些可爱的闽南孩子。
他推开窗子,立刻整个房里透亮起来。这里向东,侧对着厦门狮山,每天太阳总是从那头升起来的。
“张老师,你是一整夜没睡还是天不亮就起来了?”
“张老师,讲讲北方的雪吧,我们可是连结冰都没见过的!”孩子们唧喳起来。
“好,一定讲,以后一定讲。”他探出窗外,只见海边上那株巨大的凤凰树在晨光中象个举手过顶的慈祥沉默的父亲,让他的孩子们——满树花朵在手心上,头顶上生机勃勃地开放着……
在一片片记忆的绿叶里,也许这片算是最美的吧?
七十年代初。鼓浪屿鸡母岩下的“鸡山草堂”。
没有月光的夜,秋风拍打着那扇玻璃松动的窗子,“铮铮铮”地颤抖着。先生就坐在那张画台前,手里拿着两张画细细看着。 他年见老了,两鬓已经花白,岁月与过去的挫折在他额上开凿了几道深深的额纹。桌上这画的作者就立在他身后,强壮、卷发、留着长鬓角、两手总插在裤袋里,一条腿总晃着……
先生将画稿铺开,不动声色地挪过砚台,青年赶紧俯身地磨墨。
先生皱着眉头改起画来。他点着墨点,打着水迹烘染,边喃喃说着:“看,这里太实了,要虚一点,哎,你的气性太燥……”这时,他养的那头灰鼻子猫跳上桌来凑趣。他想赶开它,却又停了手。这头猫是从野地里拾来的。
那天他刚从牢里放出来,拖着疲乏伤病的身子慢慢走着。在一段覆盖着藤蔓的残墙脚下,他看到了这头难看的饿得精瘦的小猫。它弓背向后慢慢退缩,怯懦地打着威胁的喷鼻。
“你也碰了鼻子灰,我也碰了鼻子灰。”他不顾小猫的抓挠,拎起它的细脖子提回家来。大约就在这不久后的一个黄昏,一个过去的学生给他带来了这个一脸野气的青年。
好多年了,先生自号“鸡山草堂”的这间画室已经是门可罗雀了。从“文革”的号炮一响,他就立即成了黑帮,关押吊打饱经折磨。许多过去的亲朋好友、求画者、学画者纷纷避而远之,有的甚至落井下石。最让他痛心不解的是,那些咬他的人当中竟也有他平常最悉心栽培过的人。然而唯一能给他一点温暖的却也是他的几个学生。当他出逃时,是一个学生冒着危险把他收留在自己家中;当他的工资被扣发时,也是几个过去的学生偷偷带钱接济他的家庭。……常在这里出入的人就是这么几个人。现在,忽然又冒出了这么一个——
“你先在这里留个名吧。”先生拿个小本递给青年人。青年人不自然地从桌上抓起支钢笔,歪歪扭扭地写了自己的名字,一条腿还晃着。
“看我画画吧。”先生展开一张白纸。
画纸上渐渐出现了一座宁静的山谷,悠悠的白云,群山若隐若现;云雾中,一泉跳瀑悄然而下,在几块苍苔润点的墨石下淙淙递转;一处峭壁上悬卧一松,蜿蜓盘节,谷风动处,劲枝似微微啸动。一块虚淡的巨石上有一人危坐,俯首弄箫。一缕似有无的绵绵衷曲在静谧的画面无声地流动着……
青年人那晃动的腿停住了。他的两眼也渐渐虚开,整颗心随着这首曲子流进静静的世界,流进深沉的无边遐想……
他们的师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后来青年总来看先生作画,并向他求教。他们一起到海边散步,一起登山,但是青年人对美丽的自然景观感概不多,却总是对着世道骂娘。他和他的同龄人情形大体相似:失学、插队、没后门而干些粗重的临时工、受欺压、酗过酒、也打过架……也是一只灰鼻子猫啊·在这乱世中,一切都处在毁坏的边缘。
“心要静下来。要相信,相信世道最终是公平的。”先生只能用这种话来岔开青年咒骂,他只能用另一种特殊的方式的来保护这青年的灵魂:他利用在学校图书馆打杂的机会、偷偷地带出许多名家的画册,把米开朗琪罗、达·芬奇、高更、石涛、八大山人介绍给了这个青年,教会他怎样去欣赏,怎样去鉴别不同的艺术风格,怎样去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和艺术修养;他把杜工部、李太白的诗集借给青年,他们谈屈原、谈陶潜……这座“鸡山草堂”象根线,牵住了青年风筝一样晃荡的心。
岁月推移,在先生的画室里,不知收容过多少这样的“途中之徒”。对于当时还身为“黑帮”的先生来说,这些举动或许是出自一种道德的本能。他大概没有想到,对于青年们来说,这却成为他们一生道路中一个重要的转折。
八十年代后期。鼓浪屿海滩。
潮声在这宁静中提示着世界的不停运动。
沙滩上伸延着长长的一串脚印,先生慢慢地朝前走着。他常常来看这日出,踏着淡淡的晨雾,迎着洗心的流光。他察觉了么?这世界留给他的日子不太多了!
“每作一幅画,就和这跨步的感觉一样。”他是这样认为的,是啊,读他的一幅幅作品,总能体察出他的一步步生活和思想印迹。
……寒意萧瑟,花青为色,重重峻拔的山岩之下,无声地流着一弯凛冷的江水,江边默默地摇抖着簇簇苇草,挣顽着丛丛劲竹。水逼山压之间,披头散发,昂首曳袖、踽踽而来的正是三闾大夫屈原。他有不尽思、不尽哀、不尽言,一路神色恍惚喃喃自语……
这是先生在一九六六年画的《屈子图》。当时大字报围困着“画黑山黑水”“反动权威”的他,要抓他关他的风声已起。他和全国每一个善良公民一样对这场突然的灾难感惶恐、费解。但是此时他更希望的是得到别人的理解,“脉脉此情谁诉?”
……高岩峭壁、繁林茂树直插天际,墨块窒息了大半个画面。威压、沉闷、透不过气来。然而在峭壁脚下却悄悄松开了一曲细水。一个撑排沿水而出。那人轻舒胸臆,因前头竟有赭石的沙渚、淡青的苇草,还有数朵桃花在绿中灿亮……
这是一九七三年所作《桃源图》。其实先生并没寻到什么世外桃源,他最多只能在偷偷作画时使自己精神上得到一点解脱。可是在大半个七十年代里,他的作品中表现类似的内容非常之多:冰峰雪岭下几棵粉绿的芭蕉;肃秋的一片枯黄中几点跳动的红叶;黑天暗地里一间透出微光的小屋……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做为一个老知识分子,一个老艺术家的他是多么苦闷。尽管他被凌辱、被迫害,尽管他因此常有避世超尘之言,但是他毕竟是个人,是个红尘中的正直之人。他依然抑压不住心中那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事业的热爱、对人的一腔情。凡心不会死啊!他一直盼望那种窒息的消亡,盼望光明,盼望春天,盼望这世界“豁然开朗”而有了出路。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他只能不断地在画中造就这种希望的幻影。
……寒山解冻,积雪消融,危岭峻崖,壁露翠光。一队竹排在溪中冲开碎裂的冰棱,顺流直下。撑篙人在左点右点,峡谷里似乎腾起一片喜气洋洋的喧闹……
这是先生一九七八年所作《冰破航通图》。从“四人帮”垮台后,他就按奈不住心中的狂喜,画“时雨”、画“春回”、画“朝晖”、画“新绿”。他感到人民的好日子来了,感到放手干事业的时候已到,就连儿子贪睡迟起,他也急急作画,题为“花落无人扫,鸟啼客犹眠”,劝讽儿子们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
此后几年,他又创作了大批雄浑沉厚的山河颂歌,这些作品将他精湛的画技、深厚的功底和他个人丰富的情感及强大的品格力量溶为一炉。正是他应该大有作为的时候啊!
他的画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他的生活印迹是一幅很长很长的画。就象早晨沙滩上这一长串脚印一样。然而,这行足迹过早地中断了!
……一个劳旅之人碌碌于茫茫沙野。天际,一弯淡淡的彩虹。一队轻雁穿虹而过。朝着这飘渺的虹门,这个人正一步一步的走去……
这是先生所作的《虹门雁》。而他,永远在这幅画中走着,走着,永远在我们心中走着,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