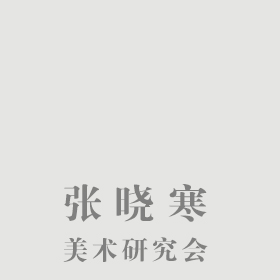怀念张晓寒老师
文/黄曾恒
老师在临终前的一段日子里频频对我说:“我真想画画呀,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画出来呢,真想能画画啊!”现在他已经逝世一周年了,这话却一直绕在我的脑子里,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念及,便感到悲哀浸到内心深处,我也不明所以。
张老师一生坎坷的经历,我能知道的毕竟太少。但我知道,这经历造就了他的品格和艺术。正如天风鼓动着海浪一般,不平的人生鼓动了他那清峻透彻的笔锋。这是自然的流露,是极高尚的境界!然而天风未息,他的笔却摧折了!“我有好多东西没画,真想能画呀!”当时,我找不出话来安慰他。

七十年代,晓寒先生夫妇与学生们一起,后排中为黄曾恒。
在我还小的时候,在我的杨胜老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张老师的画—— 一幅雪岭红梅。当时我非常惊异:这与我印象中的曲曲折折的山水画构图绝不相同——笔直的线支撑着,分割着画面,直接了当地把一切矗立在你面前!说实在,这即兴的绘画简简单单,没有任何炫耀之处,但含蕴却很深,我总觉得不能充分了解它。杨老师说:张老师是以文学之心入画的。我还小,不能体会,只觉得其笔势峻急与力量雄浑是我从未见过的。到后来,我才略微明白了张老师的构图法。他的笔力并不只在用笔中追求,定要在整幅的结构中,才能感受那寥寥几笔所负载的分量是多么厚重。你看看那些线的支点,多么坚固的构造,直如辽金大殿中的梁柱一般;再看看那些线的交织;多么明快的语言,这是魏晋清峻通脱的文章风骨。
后来,我有机会常常站在一边看张老师作画。他的方法是大处着眼,大处落墨。“一画落纸,众画随之”。因此在整个过程中往往生出不断的涟漪。这就是我所说的“即兴”。他不总像别人一样先立主景于画中,然后用其它部分作陪衬。画谱中所谓“定宾主之朝揖”,早成了一定式,人们解释说这样才能突出主题。但实际上这类定式乃出自一种对自由的恐惧心理,一种自我封闭、自我藏匿的愿望。然而张老师的画只是一味生发,主景往往很小而且不在中心位置上。看看他的杰作《怀沙图》吧,大面积的崇山峻岭与脚下不过一指高的屈原形象同属伟大,山即是人,人即是山,所谓突出主题,还有比这更突出的吗?“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鄙也”!这是庄子《齐物篇》的箴言。真正的自由的绘画,不能不体现这样的品格:不炫耀,任自然,具深心。要谈张老师的绘画,虽然头绪万端,但就举此三项,亦可得其仿佛了。
如今的画展真象是竞技场,人们在此炫技,在此竞争,比蜜峰还热闹,比园圃还耀眼。如此,张老师的画风早已被忽视了,尽管人们还热切地谈论他,纪念他。然而我相信真正沉着踏实地继承张老师的人我想一定会有的。然而,我脑子里总还是绕着老师临终的话:“我还有许多东西没画出来,真想画画呀!”当时我没能安慰他。现在自己也得不到安慰——除非我们有一日能重新拾起老师那管自然的、清峻的、透彻的笔。
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