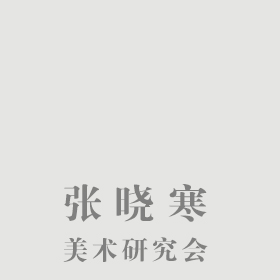与导师张云松的因缘
文/马心伯
岱宗巍巍出众山,仰脸石梯入云间。八十老太犹抬步,少壮更须奋登攀。
这首题画诗源自张云松老师为我平生首作山水画《泰山南天门》所写,时过三十多年,少为人知。适逢先师辞世二十周年之际,予以重新发表。
一九七六年初夏,我等一行赴京途中,计划游览东岳泰山,在山东泰安下了火车,抬头望去,见远处有座并不起眼的山,心想福建高山多得是,何需大老远来登这座小山,心里着实有失所望。有人说既来之则安之,我只好随大伙一同登山。连续不断的石阶使两条腿渐渐感到吃力,仿佛这山越爬越高,又没有什么景物可供观赏,于是开始萌生打退堂鼓的想法,忽见三位白发老太,手执拐杖,走在我们前面,内心为之一震,意识到自己身为中年男子,怎能不如三个老太,便迎头赶上,询问她们为何这么高龄还来登山,方知最大的老太已经八十多岁,带着两位六十多岁的儿媳和女儿到泰山祭拜泰山娘娘,她们每年都要来一次。她们身上都背着用布巾包裹的东西,有祭拜的供品,有可作干粮的大饼,渴了就喝山上的泉水。这三位老太的精神深深打动着我。到了中天门,不禁大吃一惊,面前是一片空荡荡的弥天云雾,唯见远处天空中浮现一座古建筑——南天门,仿佛真的见到天上的南天门一般神奇。这时,我情不自禁地喊出民间传统的一句俗语:“有眼不识泰山”!这种情境,至今仍然令我感慨万千。当云雾稍退,泰山象撂去罩在脸上的面纱,渐渐显露出它的真面目,这时才发现自己还在泰山脚下,真正的泰山还老远老高。泰山的雄姿和变幻莫测的神秘感使我们忘记了疲劳,它象磁铁般吸引我们加速前进。在接近南天门时,只觉得自己是在爬天梯,除了通天的石梯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进入南天门时,似乎有一股强大的风把我吹到另一个世界。从岱庙往下看,云雾已经把自己和人间分开,自己就象神仙一般站在云端。也许正是这种人间天上的奇妙境界,才使得历朝历代的帝王不辞辛劳前来泰山祭拜。这种震撼心灵的境象,促使我返校之后提笔画出平生第一幅的山水画——泰山南天门,并将自己的感受写了一首小诗,然后一起拿去请教张云松老师,请他对画稿和诗稿进行修改,这样就引出文章开头的这首题画诗。
作为一个雕塑工作者,登岱之后,我开始为山水的神秘感所吸引。对近在眼前的日光岩意境有所领悟,因此画了一张探索性的草图,到张云松老师家中请教,希望了解一幅画该先从何处下手。张老师看了我的草图后,当即拿纸提笔由近及远地画给我看,这是多么亲切和直接的启蒙与示范,使 我对山水画的程序、层次和用笔用墨有了直观的感受,对我日后喜爱名山大川和研习山水画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这幅示范画成为我的珍藏,也是与导师张云松因缘的见证。更有幸的是,此后我的住房被安排与张老师为邻,可谓天赐良机,使得我更有机会到张老师的住处观赏他那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作。他那简练概括的笔调,有力的线条、淋漓的水墨,帅气和灵性尽显其中。他的画幅不甚巨大,而画面给人的感觉却很博大。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曾建议他把画投放市场。他对我说:不卖,要藏画于民。把画送给喜欢的人,人家当成无价之宝,自然会好好珍藏, 这样,我的画就能在民间长期保存,最终成为传世之宝。我的理解是不为钱财画画,才能使作品具有高雅的品格,不使人品、画品充满铜臭味。也许这种想法有点不合时下潮流,但也无可指责,相信历史会对此作出公正的评论。
我与张云松老师的因缘不限于此,早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当我怀着一颗立志学艺的心愿,由安溪来到厦门鼓浪屿八卦楼报考时,文考官就是张云松老师,而后,我被录取并分配在雕塑专业学习,这样,我便开始了此生的艺术道路,如今恰好整整半个世纪。由于因缘所致,无论我的雕塑还是我的山水画,都与导师张云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