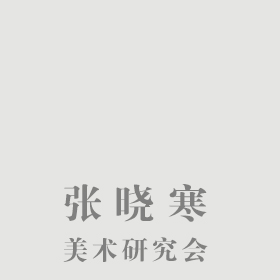怀念张晓寒老师
——老师与心源书画社的一段情缘
文/姜华
张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每当忆起他对我的谆谆教导,他对我的关心,以及我们间的友谊,我总是有些内疚,早就想把我们间的那段情缘,把他支持心源书画社,抱病到画社授课的事说一说,可无奈本人才疏学浅,笔头钝拙,几经提笔又放下,宿愿未了,今得良丰老师鼓励,只当摞列回忆。
我有缘认识张晓寒老师,是在文革后期七十年代初,我到厦门师范学校就学,当时艺校(工艺美术学校)与厦师合并在一起,原艺校的许多美术教师如杨(夏林)老师、王仲谋、孔老师、马老师、文星老师,他们都是我们的美术老师,我们也就有幸向他们学习了国画。但当时他们还处于半解放(半天劳动改造半天教学)状况,听他们的课十分有限,于是班里几位爱好国画的同学如林中立、陈仁坚和我一道利用课余时间,放弃节假日往晓寒老师鸡山的家里跑,带着作业向他学习国画。老师不但忙里抽出时间讲解,有时还留住我们在他家用餐,我的一点国画基础,也就是那时在他的手把手教出来的,才懂得一点技法。

1986年晓寒先生在龙岩矿区讲学作画
张老师画品好,人品更好。在教学中不忘“育人”;他教会我们许多道理,谆谆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他说:“知识学了是你的,学了就有用,想用再学来不及”。在他的教育下,我们整个兵团班(来自建设兵团)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晚自修时,只见我们班的教室灯火通明,大家整整齐齐地在学习、温习功课。这种认真的学习精神深得学校好评。但也有人批判我们“只专不红”。我那时是班里的班长、民兵排长、学校党支委,我记住老师的话“学生以学为主”。不参与学校里的“批”,“斗”。但学校的文体活动,我们不但积极参加,而且成绩都是拔尖的,许多项目是全校第一,即使下学校去实习,我们班也取得好成绩,深得学校好评。这在当时文革后期,突出政治气氛还很浓的环境下,不是件容易得到的事,我们这个班级可算得上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班级。时至今日,许多当时的老师,提起我们班级仍十分赞扬。
由于我们在校认真学习,业务素质高,学员毕业分配各单位后表现都很好,教学水平较高,深得所在校好评,不少同学还走上领导岗位,我也当上教导主任、副校长。

处处山歌人正忙 张晓寒 1986年
张老师不但关心我的学习,还关心我的婚事,在我临近毕业前赠送我一幅“迎风双影图” ,在画里题识“迎风双影于目前”,寄希望我“回团喜讯”。两年后我与兵团的厦门知青姑娘喜结良缘,实现他老人家的“喜讯”希望。可见老师不但学业上是我老师,生活上也关心倍至,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我尊敬的长辈。短短的学校时间相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道理,画艺在他的指导下,突飞猛进,受益匪浅,时至今日,难于忘怀。在往后几年的日子里,我们往来书信不断。在来信里他客气地尊称我为“弟”,可惜经历了多次搬家,丢失了他的十几封信件,实乃一大憾事。在信里,老师鼓励我把周围画画爱好者组织起来,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在老师的亲自过问和关心下,“心源书画社”于一九八四年春正式成立了(我任画社社长),张老师为了支持这新生群众团体,一九八五年冬应我邀请来到了龙岩,给我们画社讲课,给矿山工人授课,并深入矿山基层写生作画。怕他年老体弱,经不住山区寒冷,我没想带他下矿,可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我只好带他到坑柄矿。可距要去的矿井有三十多公里,那天正巧局部小车紧张,一时没车送他,他又急着要下矿,我只好用我的“重庆八十”摩托车载他下矿。就这样,他坐着我这台“牛车式”的摩托车,饱受风寒下矿。当他看到下班矿工满脸沾满煤灰,只露出洁白牙齿和疲惫的双眼时,不禁潸然泪下,连声说:伟大!伟大!他们最伟大!并当场以矿山煤台为背景,作了一幅“矿山处处紫金开”国画送给煤矿。在矿山其间,他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绞车房、矿灯充电房、澡堂、食堂。这次龙岩行成了他最后一次基层活动,也是他抱病坚持教学的高尚精神。当时他饭量很小,告我说是胃肠不好,我杀了只鸽子想让他健胃,那曾想,他根本吃不下。事后才知道,其实那时他的病灶已在发作,他是抱病前来的啊,悔不该让他老人家来遭这份罪。

1986年晓寒先生在龙岩矿区书画爱好者在一起
在后来几年书信里,老师时常过问画社建设,过问学员的画艺,一再嘱咐我们要多画,多实践。他说:“矿山体裁就是最好的体裁”,让我们“多画身边这些伟大的矿工”,并推荐著名国画家章玉山辅导我们。一九八六年心源书画社举办“成立一周年书画展”,张老师特地送来山水画一幅致庆,并题识:“龙江上游接汀江,处处山歌人正忙”。老师对基层群众美术团体的爱护,对美术爱好者的支持,如此热忱,让我们十分感动。从此,画社活动蓬勃发展,学员队伍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成为闽西一个较有影响的画社。当时任龙岩地区文联主席的张维、群艺馆长张铁强、黄云裕等领导曾为画社的“书画展”剪彩。正当我们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回报老师的殷切关怀,拟举办“龙岩地区职工书画展”时,传来老师病故厄耗。消息传来,大家震惊,悲恸!回想德高望重的老师不辞辛苦,冒着寒冷,抱病到山区来辅导我们这些初学者,为画社的建立,为学员的学习耗尽他最后一滴心血。此情无以报答,此义终生难忘。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激励年轻人好好学习,热忱辅导学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他的画风,他的高尚人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