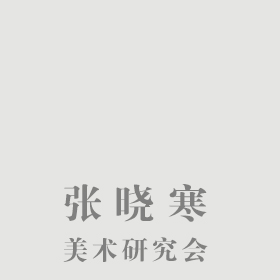心潮逐浪——忆晓寒老师
文/戴礼舜
晓寒老师竟然仙世二十周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蓦然回首,我进工艺美校就读至今,也已三十年整了,然而,住昔的情景依然清晰。
一九七八年春,我考入艺校,从家乡莆田来到鼓浪屿,年青人的求知与好奇,使得我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无比的亲切,由于进校前,我就喜欢并学习过国画,所以对学校里的国画老师特别的关注,当时,学校的老教师数晓寒老师最有风度,也最健谈,但是,在他笑咪咪的脸上,总是透出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那份威严。那时,我们班教室的隔壁就是绘画科的办公室,有一次,学校请马应瑞先生装裱国画老师的部分画作,就在科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晓寒老师的山水画,简约,清新、典雅的画风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给我的感觉是,晓寒老师是一位深具诗心傲骨的老师和画家。
由于对晓寒老师的敬畏,每次遇到他,我都会主动问好,他也总是点头示意,及至二年级时,他上我们班的山水画课,我才得以进一步亲近晓寒老师,也便有时常到鸡山路老师的家中拜访和小坐的机会。老师上我们的课没几天,全班同学的名字他不仅都能叫得出,而且还知道是哪里人,有一次,我请老师示范画法,他画了一张溪边小景,末了,在树上点了些小红点,边点边说:这是你们莆田的荔枝树,莆田别称荔城是吧!是水果之乡,也是文献名邦,你们那边的人都很会读书,也很聪明,莆仙画派是很了不起的。一番话,说得我既自豪又惭愧,更是激励我发奋学习。晓寒老师讲课富有激情,其抑扬顿挫的语调,旁引佐证的论述,极具生活化的比喻,把奥妙无比的画理、画论深入浅出地阐明,常常使我们听得陶醉。在晓寒老师上我们课的同时,刚好我们的文化课是教授古诗词,但文化课老师在讲解古诗词时,每讲到一首诗的核心处,便说:“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意思。”弄得所有学生一头雾水,不知所从,似懂非懂。有一次,当我们向晓寒老师反映这个问题时,晓寒老师说:你们要尊重每位授课老师的讲授方法,古诗词是要靠领悟的,只有自我领悟出来,才是深刻的,才是真正学到知识。自此,每当我阅读古诗词或古文时,老师的这句话总会回响在耳边。
晓寒老师在文革后期曾同小龙等人攀登厦门虎溪岩,对虎溪岩的景物很钟情,他总是说,虎溪岩石最能代表厦门山石构造的特征,块垒森严,大气磅礴。老师上我们山水画课时,就特地带我们到虎溪岩写生,那天,我们自备了干粮,还准备了些地瓜酒,一大早从鼓浪屿过海前往厦门写生,当时虎溪岩尚未开发,荒草丛生,荆棘塞阻,老师与我们一起穿行其间,中午时,觅得一块空地,大家围坐着用餐、小饮,老师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并高歌岳飞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高吭的歌声回荡在旷壑间,我深深感受到老师身上所特有的那种文人气息及其重返教坛,一吐胸中块垒,喜获自由的喜悦心境。
那时,我们虽说是就读工艺美校,但同学们都没有从事工艺美术的概念与志向,总是自觉与不自觉地认为是在纯绘画的美术院校学习,毕业以后能当个画家,我们绘画科的课程,也是以国画作为教学重点,所以,到了上工艺课的时候,什么通草画、软木画,全是民间工艺的学习与制作,我们满腹的委屈,似乎有一肚子的苦水,当我们向晓寒老师诉说时,老师一方面耐心开导我们,说明工艺美术是学校的办学宗旨,另一方面,继续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以后能在不同的行业有所作为,并说:“我教不出那么多的画家,你们能有一两个是大画家,我就很满足了。”现在,回想老师的这句话,真是惭愧。
在艺校读书时,我才十几岁,年轻气盛,不谙事理,所作人物画有一些独特的思路,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经常会将学校老师的作品与当时中国画名家的作品相比较,因此,对某个老师的画颇有微词,也因此而得罪了老师,日后更是带来了诸多的麻烦。晓寒老师知道后,在批评我的同时,说我对很多事情不能“不求甚解”,要透彻学问,透彻世事,不断地完善自我,充实自我,从各个领域丰富自己的学养,最令我铭心的是他说过的一句话:“画不惊人死不休”,如此的格言,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这句话,也是晓寒老师自己的写照。
一九八一年春,我即将毕业,临行前,至晓寒老师家辞行,并希望老师能留幅墨宝给我作为纪念。老师当即画了幅画送我,画面上惊涛拍岸,中景的礁石上站立几个人,远处潮水涌动,征帆片片,几只海鸥翱翔其间,画上题了:“心潮逐浪,礼舜同学沧海征途正宜努力,晓寒为画”。是啊,在校三年的学习与生活,与老师、同学的朝夕相处,如今将告一段落,将告别学生时代,走上工作岗位,这是迈向社会的第一步,也是今后学习的起点,此时此刻,心情如何能以平静,惜别与憧憬同在!晓寒老师借用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词里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句,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境及展望新生活,在未来的学习与工作上的鼓励、祝愿蕴含其中,此画即情即景即寄望,实为佳构。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莆田涵江工艺三厂工作,是从事生产雨伞和筷子的美工设计,良丰弟则被留校任教,跟随晓寒老师学画。每次到厦门,我常常会同良丰弟一起,抽空到鼓浪屿鸡山草堂拜见晓寒老师,到钟楼脚下拜见王仲谋老师,他们总是鼓励我不要气馁,在小天地里要有大作为。后来,良丰弟画了一幅武夷慧宛图送我,晓寒老师还特地在画上题跋:“武夷慧宛香润润,良丰所作赠礼舜,亲同手足好情份,辛酉春晓寒为题。”时间飞逝,一瞬而过,往事并不如烟。
一九九八年,良丰弟等人筹备成立“厦门市张晓寒美术研究会”,我义不容辞地成为研究会的忠实会员,十年间,研究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成绩斐然,同仁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使很多人感动,如今,《怀念张晓寒先生》文集即将付梓,约稿于我,勾沉往事,沧海征途,心潮逐浪。
二○○八年三月于涵江觉如精舍